为朋友的新书写序----“等一等灵魂”
小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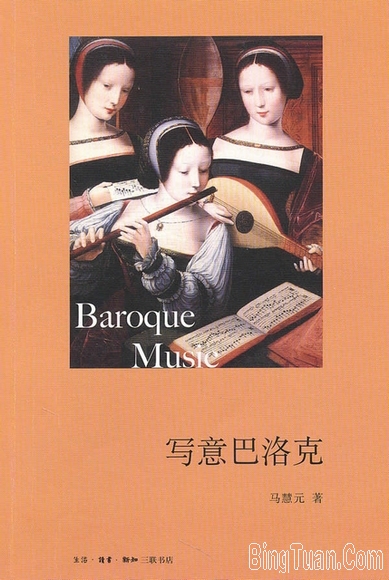
序
大部分人挤在所谓时代列车上,气喘吁吁,心急如焚,尽管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义无反顾,只嫌不够快。
少部分,不,极少部分人,在那磨得有如利剑一般的铁轨旁边走着相反的乡间小路,按照他自己的节奏。也许正因那一辆辆挤满乘客的列车速度过快,使这悠然的步态也显得颇有些锐感,它穿透所有的烟雾尘土,径直探入那些深藏奇妙的地方去。一切烦人的嘈杂于这些人似乎并不存在,前方自有青翠天地豁然敞开。
放下繁重的工作,于灯下捧读马慧元的音乐文字,心会立即静下来,变得干净、温润、安详、单纯。听她与音乐大师们对谈,轻松愉悦中时时跳出精妙言论,悄然浅笑间却又带出历史积淀,真是一大享受。看她轻轻翻开已有些发黄发脆的谱页,请出那些双手仍然温暖笑容依旧亲切的大师们,一同谈音奏乐,恍然间抬眼望出去,那不是从未污染过的田野和山丘抑或古老的巴西里卡吗?
音乐究竟是什么?如何言说?在音乐学院教书那么多年的我却越发困惑,越来越觉得教人听音乐、爱音乐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之一。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音乐是一种心境》(《艺术世界》1994),虽非学术探讨,但文章立意在今天看来仍有道理。历代作曲家是在怎样的心境中写下点点音符?与之相隔巨大时空的我们,又在怎样的心境中与他们相会?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听觉和心灵之间,如何达到神秘的共振?我最后写道:
“什么时候,你同这些作曲家、演奏家和演唱家成了朋友,什么时候,你听见了他们在音乐中向你诉说的一切,什么时候,你获得了涌遍全身心的、无以替代的激情,我想,你就绝对是一位听音乐的内行了,因为你找到了他们的心境,也找到了你自己。”
假如有人进一步追问:这个“神秘的共振”,这个美妙的“什么时候”,在哪里?如何获得?我深知,仅仅是鼓励解决不了问题,“可遇不可求”、“音乐是不可言说的”、“听音乐是极其个人的事”都是不负责任的托辞,但我手里的的确确没有万能钥匙可以送人!所以马慧元请我写这篇序言时,我第一反应是写不出来,回绝了。这位小人家很固执,谆谆教导我说“音乐欣赏课还是重要的,因为它给有愿望、听觉有基本敏锐度的人梳理了方向——对我启发就很大。”她举出我非常敬佩的Joseph Kerman为榜样,告诉我她眼中好的和不好的音乐欣赏课是怎样的,又把耶鲁大学教授Craig Wright的网上公开课链接给我看。这是很长的一个系列课程,仅仅看了个开头就知道非常精彩,但我匆匆瞥了几眼就放下了,实在是怕把我自己的脑子搞乱了,那就更写不出来了。
既然逃不掉这项作业,不如在讨论中整理一下思路。
面对一部音乐作品时,听者常会在两条轨道之间磕磕绊绊,一边是专业性技术分析,另一边是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前者看上去很枯燥,那些调性、和声、织体、曲式分析就像是一把把冰冷的手术刀,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将作品细细解剖,最终将一切简约在一张化验报告似的图表中;后者很迷人,音乐大师一生的爱恨情仇,他所处时代的思潮或事件,民族的悲壮命运……但倘若沉浸其中,却常常是思想信马由缰,音乐虽仍旧鸣响,但听者的涟涟泪水已与音乐毫不相干了。
我说,我很怕那种对音乐没感觉只是一脑门子技术的人;马慧元说,她怕的是那种心灵至上而蔑视技术的人——我们反对的都是自己环境里最常见的现象。我面对的是被艰苦的技术训练磨掉了柔软触角、失去了原初热情的音乐学院学生,她面对的是缺乏音乐操作实践、热情高涨却总是隔靴搔痒的爱乐人。放下那句“可遇不可求”的托辞,在两条轨道中间架起桥梁的,应该是什么呢?
语境。这个词是讨论中她提出来的。我说的是“一次作品赏析应该是一次音乐学分析”,再加上我之前所说的“心境”,于是,赏析的过程可以是这样:将音乐形态或“符号”——诸如舒缓或急促的节奏,厚重或轻薄的织体层次,高高飞扬或谨慎蜿蜒的旋律进行,跌宕起伏或平缓松散的结构,截然不同却并行不悖的乐思,都放到它们的语境中去理解,让那形态各异的音符还原为历史空谷里的回声,还原为作曲家的心灵搏动。譬如藤蔓般环绕着女高音咏叹调的独奏小提琴是怎样跳出了巴洛克时期占主流的宏大叙事风格,在一首辉煌的大合唱之后,将简短的“我们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转换为个人内心的呼唤,温柔欣喜甚至私密亲切的赞美;固执重复十三次的哀哭般半音下行固定音型及复杂的和声,又是怎样把简单的陈述“在彼拉多统治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营造为令人心碎的情境,将听者带到当年的髑髅地;曲终时又是如何在“埋葬”这个字眼上用升高的三级音将之前的厚重阴霾一扫而光,昭示即将到来的复活之日(以上例子均选自巴赫b小调弥撒曲)。
作为音乐学院的老师,我肯定会用专业技术词汇来谈论音乐,而聪明的马慧元则完全不依赖它们,巧妙地也极其体贴地,将她细腻灵动的个人感受与深度阅读、广泛赏乐乃至日复一日的键盘操演体会,自然流畅地融合在轻松的笔调里:
“……他还讲了库泊兰等等句子的弹法,因为乐器局限以及习惯,什么音要保持,跟乐谱记载是不同的。……我这才感到,再怎么读谱,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我又追问,“请问你对兰多芙斯卡怎样看?”他大摇其头,说兰的琴压根不能算羽管键琴,我说是啊,真想象不出她怎么用那么大的力气弹琴。他说,兰在当时喜欢上了那种音乐,就自己想法设计来实现音乐,但那跟羽管键琴的观念完全不同。”
寥寥数笔,就将乐谱的局限性、不同时代的音乐风格、羽管键琴和现代钢琴的风格区别、本真和创新两种不同的阐释观念等等,轻轻松松地传达给了读者,还一不留神似的,把一位自然率性的演奏家带到眼前,以后再听兰多芙斯卡,你也许会觉察到她以独有的灵性赋予传统音乐的一份清新。又如:
“我们的文明认可的价值观,大概要包括这个:有结构,充分展示匠心,才能被视为杰作。而这个中世纪传说似乎就是这样的,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满不在乎地一个个发生完毕。
也许,这就是中世纪被当成“黑暗”时期的原因?或者,这是未被体系化的口述文学的特点?不知道。我只隐约感到,这个时期的作品,除了故事情节之外,显得跟古代、现代都没有形式上的明显联系,它从一个有机体上断裂开,无法进入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以后的价值体系。它只能自成一体,在后人眼中显得粗糙而有力。
不过,还是感谢音乐吧。它软化了我追索历史的欲望不说,历史此时呈现出另一种维度,和音乐、艺术若即若离。耳朵有权拒绝历史。”
正如好的音乐作品会带给每个人不同的体验,好的文字也一样。读者尽可以不理会我上面的罗嗦,直接翻开后面的篇页,随同这个秀外慧中的女子,这个从大二就开始在薄薄信纸上用娟秀细密的钢笔字和我聊听乐感受,如今已经能在庞大的管风琴上手不忙脚不乱巍巍然演奏巴赫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565)的马慧元,开始迷人的乐林漫步。
印第安人有句话好像是说“等等灵魂”。说得好!我们都别忘了在自己尚可把握的时间里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在相遇的那一刻,甦醒。